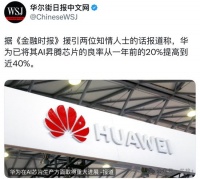我的保洁阿姨,在北京买了套房
如果你是一个足够细心的人,可以观察一下每个公司下班后的洗手间。
当一个公共区域的保洁阿姨下班之后,这片区域不出半个小时就会一片狼藉。
即便是在一栋精英云集、学历985起跳的写字楼里,没有这群劳动者的维护,厕所也会卫生纸横飞,尿渍满地。
这时候我们才意识到基层劳动的意义:他们的存在是隐形的,似乎都长着相似的脸。然而,一旦他们不存在,高速前进的社会将会瞬间瓦解。
在这一捧沉默的螺丝钉里,这群基层女性被叫做“阿姨”。
她们是谁?她们过着怎样的生活?有哪些忧虑与快乐?
我与两位素不相识的保洁阿姨展开对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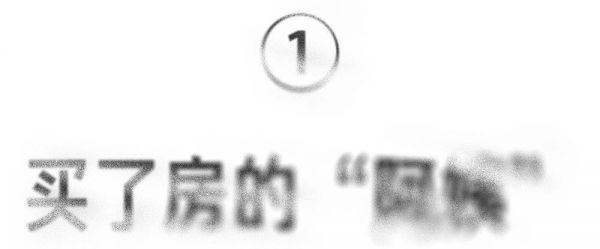
和小时工赵阿姨对话的时候,背景音非常嘈杂,能听得出来,她使用着一部不太好的手机。
65年生人的赵阿姨,今年59岁了,和我的父母年纪相同。她的丈夫是一个电工,两个人在北京已经打了15年工了。
来自河北的她,工作区域集中在北京石景山一带。
据赵阿姨回忆,刚来北京打工的时候,小时工的价格还是7-8元/小时,如今随着物价,已经上涨到了50元/小时。
每天早上4:30,赵阿姨忙碌的一天开始了。她在北京西郊的一所单位食堂打工,负责在后厨做饭。忙活到中午12点之后,食堂的活儿做完了,她就骑着电动车开始去各家各户做小时工。一直做到晚上9点,天已经黑了,赵阿姨再回到单位的小宿舍间里,随便吃点东西便睡了。
赵阿姨每个下午可以做3-4户人家的家务活,每户人家做2个小时的工,客户按照1小时50元计费。一个月下来,赵阿姨可以靠小时工赚到7000-8000元,加上单位食堂帮工,每个月可以拿到1万元的收入。客观来讲,这份收入比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要可观得多。
这份工作之所以能带来如此丰厚的收入,得益于赵阿姨在北京打拼15年来积攒的人脉。老客人看她做得好,就为她介绍新客人,靠着人传人的口碑在北京站住了脚。
赵阿姨回忆起来,这些年走走停停,总共给四五十家人做过小时工,有人搬家离开了,有人带着孩子出国了,有人离开北京了回老家了,来去匆匆间,只有赵阿姨留了下来。“刚来到石景山的时候,这里还是土堆,现在完全变样了,我是看在眼里的。”
这15年来,她没有加入过任何家政公司,一直以独立的小时工身份游走在石景山附近的各个家属院。“之前也去家政公司试过,但阿姨太多了,根本排不到活儿,一年还要给公司交几百块钱年费”,为了能赚得更多,赵阿姨再也没去过家政机构。
做“阿姨”这一行,她见到过各种各样的家庭,也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。
赵阿姨最头疼的,就是打扫油腻的厨房。她总结了一些经验:要先用小铲子,趴在厨房一点点把硬了的油污铲掉,然后再用配好的清洁剂擦一遍。一间厨房清洁做下来的劳动量,相当于打扫了三户人家。遇到这种情况,两三个小时也不一定做得完,但多出来的时间,大部分客户并不会加钱,“花钱的都是客人,没有花钱的错处”,赵阿姨朴素地笑了笑,表示自己并不在意这些。
从声音判断,她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中年女人,说话缓慢温和,谈起奇葩的客人,也只是淡淡的几句,没什么太多委屈的情绪。
如果一定要说那种客人最难应对,那一定是老年人。
有些老年人会对来家里干活的阿姨说一些刺耳的话。他们也许是糊涂了,也许是年老之后产生的不安全感,对上门干活的小时工产生了抵触情绪。赵阿姨从来不会回嘴,都是左耳进右耳出,也不会再和人赌气了:“如果是我年轻的时候,可能还会理论几句,现在有经验了,我知道老年人是最不能说的,一旦出了什么事儿,赔一万个我也担不起责任。”
赵阿姨也总结了照顾老年人的经验:一切都顺着他们。只要顺着他们,他们也会变得很好相处,甚至很慈祥。
在一个部队家属院里,就有这样一位老人,赵阿姨每次上门,老人都不急着让她干活,而是不停问她“吃饭了吗”“肚子饿不饿”,每次都会招呼她先吃些点心,喝杯茶。
而她最介意的情况,不只是那些站在上层阶级角度刁难小时工的客人,而是那些“盯着她看”的人。
她不能理解的是,明明自己的业务很熟练,却总是被人当作“佣人”和“闯入者”看待。“我干活还是挺干净的,从来没人说过我干活不干净,我是比较认真的。但总是有人跟在我屁股后面,生怕我偷懒,或者怕我拿了什么东西。”
赵阿姨描述不清楚这种模糊的感觉,只是隐约发现“自己没有被尊重”。她也有自己的处理方式,那就是用各种方法拒绝再去这样的人家干活。
但在赵阿姨看来,世上的好人还是占多数。
有人在过年期间,给上门干活的赵阿姨送了大包小包食物和特产,还有人给她包了200元的红包。
在一个老家属院里,有这样一户客人,平时上班不在家,就把家里的钥匙给赵阿姨也配了一把。约定好时间后,赵阿姨可以自己上门干活,干完活还可以在客人家里休息一会儿,一百块钱会按时出现在桌子上。这些难得的信任感和尊重,让她一直反复念叨:“这是特别好的人家,我在心里谢谢他们。”

图片由Midjourney生成
赵阿姨有两个孩子,如今都已经结婚成家了。
儿子在张家口送外卖,女儿在涿州的一家超市做收银。一家四口人分隔三地,只有过年能见到面。孩子们都有了自己的生活,赵阿姨也只是远远望着他们,然后继续埋着头为了后代赚钱。
当我问起儿女有没有让她提前“退休”,别再干小时工这行了,她也只是笑笑。“他们也说过不让我干了,我就反问他们:我不干,难道你们给我钱养老吗?”
能多给儿女分担,就一直劳动到干不动的年纪,这是许多普通中国父母的样貌。他们不发一语,走在无数个漆黑崎岖的路上,为了几十块钱起早贪黑。
出来打工十几年,老家的朋友也都离散了。现在赵阿姨的朋友,都是在北京打工认识的同行。“当时出来打工的时候,老家还没有通讯设备,出来以后没怎么回去过了,所以再也没有联系。”
和大多数60后们一样,赵阿姨的生活只剩下了赚钱和攒钱。
她告诉我,自己平时没有休息时间,也没有什么业余爱好,同龄人跳的广场舞她一次也没跳过,她给我的理由是:“连吃饭和睡觉都是挤时间,哪有功夫玩那些”,这是一份结结实实的辛苦钱,赵阿姨把自己称作劳碌命,一辈子闲不下来,手上永远在干活,哪怕闲下来一会儿,心里都会别扭。
在谈话的结尾,我询问赵阿姨这15年攒了多少钱,她有点谦虚地说:“也没攒下来什么钱,就是在顺义买了套房子。”
但这套辛苦攒钱买下来的房子,赵阿姨和丈夫也没舍得住进去享受晚年,而是转手出租了,因为“这样能攒下来更多钱”。
他们宁愿挤在单位狭小的宿舍里,继续走在奔波的路上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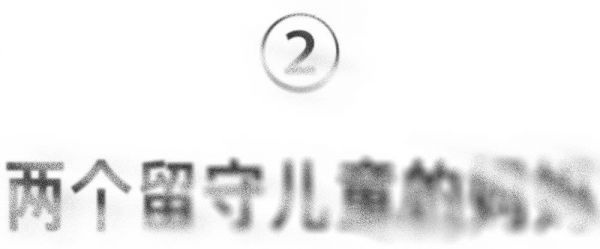
如果说赵阿姨是游走在“系统外”的游击队保洁员,那么更多的保洁阿姨,仍然困在中介与劳务公司的管理之下。
见到保洁员李阿姨的时候,她正坐在朋友家门口玩手机,脚边是保洁公司配套的水桶、抹布、清洁剂和地刮。
这是李阿姨第一次来到朋友家做保洁。上一位保洁阿姨离职之后,李阿姨按照公司给的排期表,接管了这间70平米出租屋的打扫任务。
李阿姨的面容看上去有些憔悴和沧桑,像是50出头的年纪,但实际上她是82年生人,今年只不过42岁。生活对普通人而言,从来都没有那么温和。
李阿姨来自河南南阳,初中上了一年,便开始出门打工了。
“我的父母都是种地的农民,小学都没上过,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,他们不知道上学有什么用处”。父母很早就不再供她上学了,省掉一个孩子的学费,就能给全家多省出点粮食钱。
和丈夫结婚之后,两个人在深圳打过工,生活了几年后又来到北京。李阿姨告诉我,外出打工的河南人,要么往北,要么往南,这两个城市是他们最集中的区域。
做保洁之前,李阿姨进过工厂,也做过饭店服务员,她自嘲“没读过书,只能干这些”。
在服装厂和电子元件厂里,李阿姨做的是流水线工作。工厂的机器不能停下来,工人们只有两班连轴转,才能维持流水线的高速运转。
“一屁股坐下来,手上就要开始忙活,紧赶慢赶地干,一旦你的手慢了,东西很快就会堆住,在你下面的人还会抱怨。”
工厂流水线一天需要干10个小时,人手不够的时候,顶12个小时的情况也有。即便如此,李阿姨还是觉得,保洁这份工作比工厂流水线还要累。
每天早上6点半,李阿姨会准时醒来,在家里热一些馒头当做早饭,骑着电动车开始了一天的工作。在她分管的区域,每天要打扫10户租户的卫生,有合租房也有整租房。直到天彻底黑了,9点多才能下班。
我问李阿姨如何解决每天的三餐,她告诉我,为了省钱,从没讲究过这些。
“像中午饭,我很少能坐在饭馆里吃,就在路边买个饼。有时候自己带点饭菜,就坐在楼道里凑合吃。就是为了省钱,搁饭店里买个饭,最少也要花十几块钱,还吃不饱,你像我们干体力活的,一顿饭就能吃20多块钱,哪敢下馆子啊。”
虽然住在北京朝阳区的繁华区域,但李阿姨租的房子,每个月只需要1000元租金。
原因很简单,她住在老破小旁边环境更差的平房里。我曾经走访过这片区域,住户大多是基层劳动力。没有厨房,只有简易搭建的电磁炉,厕所是室外公用的,没有洗澡的地方,房顶是破旧的瓦片,窗户是木质的,似乎用力一拉就会损坏。不到20平米的空间住着一家三口,虽然简陋,但至少给了他们留在北京谋生的机会。
李阿姨告诉我,住在旧平房里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暖气。在北京的寒冬,气温能降到零下十几度,她唯一的取暖方式就是一个插电的小太阳,“就是硬扛,要么把所有衣服和被子都盖上”。

图片由Midjourney生成
和游击队小时工赵阿姨不一样,李阿姨的劳务身份由公司管理,所以她没有选择客户的空间,公司分配了哪家,就要去哪家干。
有一个合租房,三家合租室友像商量好了似的,把垃圾堆满了公共区域。每周的外卖袋子、快递盒子、生活垃圾、饮料瓶子,全部都丢在地板上。李阿姨每次上门,光是扔垃圾就要上下跑好几趟。这还不是最麻烦的,每次打扫完卫生,这家住户还会给阿姨打差评,长此以往,阿姨们都不愿意去这家打扫卫生了,公司也把这家租户列为特殊名单。
还有一个性格古怪的租户。两口子住在一居室里,面积不大,只有50平米,却要约3个小时的保洁时间。
李阿姨也纳闷,结果上门之后才发现,3个小时都少了。租户搬了一个板凳,坐在李阿姨身后,监督她把每一个角落的灰尘都打扫干净,窗户缝里的灰,要用手指一点点剋出来,墙面和天花板也要全部擦干净,如果发现还有一点灰尘,就要让李阿姨返工再来一遍。
租户一边监工,一边和李阿姨抱怨,要不是因为自己腰不好,绝对不会让保洁来打扫房间。
李阿姨越说越激动,她回忆起自己帮另一位租户擦书架的事。架子上杂七杂八的东西摆得满满当当,“是一些娃娃”,我猜她想说的可能是手办。一旦她碰了书架上的手办,租户就会发火,“简直一毫米都不能移动,必须给他放回原位。”
还有的租户养了猫,家里到处都是猫毛,李阿姨想用湿抹布拖一遍,租户却要求她用苕帚扫。但苕帚扫不起来,最后只能是猫毛满屋子乱飞。消毒水倒少了,租户说她偷懒,消毒水倒多了,猫一闻又吐了,无论怎么做最后都会被租户投诉,“现在的人,动不动就给差评,因为他们知道差评能扣钱”。
让她最印象深刻的,是一个性格古怪的人。李阿姨咬牙切齿地说:“他一定是个日本人,那个‘害劲’(方言,可憎的样子)我到现在还记得。”
这个怪人租户,着急了就会带脏字骂人。李阿姨打扫厨房的时候,不小心碰到了净水器龙头上的一个塑胶头,租户大发雷霆:“你知道这个东西在国外买的有多贵吗,你弄坏了赔得起吗?”就连冰箱门也不能随便碰,正大光明地歧视上门的每一个保洁阿姨。说到这里,李阿姨嗓门突然高起来:“我觉得他就是装,有几个臭钱有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说到激动的时候,李阿姨控制不住开始讲河南方言,甚至还冒出了几句脏话。刚开始谈话的时候她还很内敛,只用了半个小时她就完全放开了,双手挥在空中,像是和熟识的朋友咒骂工作中遇到的糟心事。
但她遇到的也不全是坏人。
她记得在一个合租房里打扫卫生的时候,遇到了其中一户女孩。女孩和她攀谈,才发现两个人是老乡。女孩有时候在家烙饼,也会留李阿姨吃一顿老家的饭,两个漂泊在外的河南人边吃边聊。
还有租户在过年的时候,留李阿姨在家吃饭,给她煮了一大碗饺子。“社会就是这样的,人有好有坏,形形色色的,我们都习惯了。”
除了公司已经安排好的租户保洁工作,加上其他网上预约的客户,按照每个小时55元计费,“公司还要抽成,每个月头拱地玩命干,可以赚8000-9000元,没有五险一金。”
和年轻人的消费习惯不一样,李阿姨选择“只进不出”。她平常很少买肉吃,顶多买点鸡蛋补营养。
除了生活必需的花费,她这几年没有买过衣服,也没有用过化妆品和护肤品。有时候客户会把淘汰的旧衣物送给她,她很高兴,虽然日常她根本没有时间穿工作服以外的衣服。

图片由Midjourney生成
李阿姨的丈夫在昌平的建筑工地做安全员,一周回来看她一次,算得上某种程度上的“周末夫妻”。李阿姨总结了自己的心得,丈夫至少有一个中专学历,所以能找到更好的工作;而自己没有文化,在市场上找不到体力活以外的工作。
而她的两个孩子,一直留在河南的农村,是留守儿童。
十年前,大女儿刚读三年级的时候,夫妻两人就外出打工了,那一年小儿子刚刚会爬。现在,年迈的爷爷奶奶在家看孩子,也没能力辅导功课,农村没有辅导班,全靠两个孩子自学,李阿姨有一种听天由命的无奈。
李阿姨在北京打工十余年,孩子们也只来过一次北京。她还记得当时和丈夫一起,带着孩子去看了故宫和升旗,其他的景点和商场,她这十年从来没有踏入过。“要不是孩子来,我们是不会抽空去那些地方的。有时间肯定先干活挣钱。”
大女儿今年高考,远在北京的她,只知道女儿数学成绩不好,选了“全文科”,有些烦恼孩子未来怎么找工作。她看到平时上门打扫的客户,都是“学习好的年轻人”,“这些年轻人学历那么高,来了北京也是吃外卖。”
她也在为女儿做打算。如果女儿能考上本科,她不想让女儿来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了,这里是人中龙凤竞争的地方。普通孩子去个中等城市,就不要像父母这样吃苦了。
“我在北京吃的这个苦,她吃不了,她连地铁都挤不上去。如果她以后考不上好大学,想干我这种工作,她也干不了的。我们这代人干这种苦力活,就是为了让下一代不要再干了。”
李阿姨告诉我,在老家农村,这种“留守老人+留守儿童”的模式很多。李阿姨家的二姨就是这样,三个儿子都外出打工了,留下来了五个孙辈,老人下地干活的时候,只能把孩子背在身上,或是支一把雨伞,把孙子们放在伞下面。
说起来孩子,李阿姨自顾自念叨着“这些年光顾着赚钱了,大家都是没办法”,毕竟在老家县城,也只能继续做保洁和小时工,一个月下来连3000块可能都挣不到。
“有办法的人都留在老家了,他们有门路。我们这样的普通人,只能硬着头皮出来打工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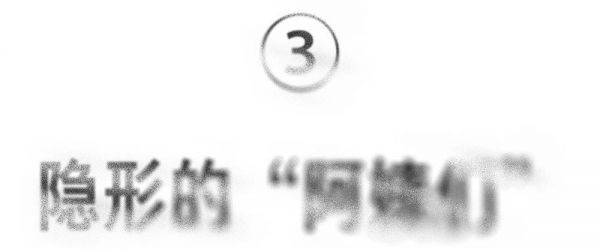
我们太容易错过“保洁阿姨”的面孔和声音。
我在写字楼里观察她们时,看到她们缓慢的步伐已经无法行动得太快,腰上挂着清洁腰包,上面还别着一部对讲机。偶尔在楼梯间和洗手间的椅子上,她们坐在那里偷闲休息。如果凑巧赶上了写字楼管理人员巡逻检查,还会看到年轻的装着制服的男男女女,对年迈的保洁员们进行批评和教育。
在了解了保洁员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强度之后,我会留意写字楼和商场的公共区域。一片反光的地砖,可能需要庞大的人力去维护。保洁一天不上班,一家公司就会因为垃圾而瘫痪。
如果没有清洁需求,恐怕没有人会和她们主动搭话,也没有人好奇她们从哪个县城走到了这里,更没有人好奇这些女人背后的故事与家庭。
她们之中,有的故事布满苦难。
一位保洁阿姨告诉我,有人为了躲避家暴,在大城市的合租屋里隐姓埋名,靠保洁工作维持生计。
也有人的故事是温暖的。
曾经有一位大厂员工和我说,在高强度的工作空间里,公司里的保洁阿姨就像不敢打扰高三孩子学习的“妈妈”,她们轻轻地走过来,收走了垃圾,又轻轻地离开,生怕脚步太重打乱了年轻人的思绪。
午饭时间她们也会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,“学习这么好的孩子,长大了还要在公司加班”,保洁阿姨看了也于心不忍。

图片由Midjourney生成
虽然保洁阿姨们来自不同的地域,挣着不同的钱,但她们身上有极为相似的特点——
她们无法忍受空闲,出售一切可以支配利用的时间,换取或多或少的酬劳,然后开始异常漫长艰苦地攒钱。
要么为了养老,要么为了留给孩子,要么为了家庭。许多保洁阿姨家里不止有一个孩子,如果生了儿子,她们的负担自然而然就会变成了“给儿子攒彩礼钱”,背后隐形的鞭子挥舞得更加用力。在她们身上能看到高度浓缩的东亚性:勤劳,吃苦,认命,不抱怨,密集地劳动。
在对谈之外,还有更多的保洁阿姨在沉默地劳动,她们的生活状况各不相同。但可以确定的是,她们没有留给自己空闲的时间。许多阿姨选择在过年期间继续接活儿,和外卖员与快递员相同,这一系列基层工作都处于计件工资制度之下,没有假期,越是节假日越忙,平台和机构会作为中间商赚差价,“劳动者-资本-客户”形成了稳定的三角形。
家政与保洁劳动,作为家庭私人领域的清洁、照料、烹饪等再生产劳动的市场化形式,蕴含着公共与私人、经济活动与亲密关系、专业主义与情感依赖的多重张力。性别机制、社会阶层和情感劳动等多重因素,都在她们的劳动过程中发挥着微妙且复杂的作用。
然而,回到生活中去,基层劳动者对阶层的理解,就是爱憎分明的“好客人”与“坏客人”,以及那一句“花钱的人没有错处”,他们自行消化了大城市中遍布的歧视与冷漠,这就是劳动人民对“阶层”二字最直观的感受。
超一线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打工基地,这里汇集了天南海北谋生的人。写字楼里高学历年轻人在打工,服务这些钻进电脑里的年轻人的保洁员也在打工,我们共处在同温层之中,却仍然很难有机会展开对话。
城市留给“阿姨们”的空间和时间也在缓慢压缩。
李阿姨告诉我,公司对保洁员的年龄要求在48岁以下,如果看着年轻,50岁也可以糊弄过去。再老一些,市面上留下的工作便不多了,到时候恐怕就只能回老家。
她要赶在倒计时结束之前,再多干几年,再多攒点钱,才能安全度过没有养老金的晚年。
相关推荐
在城市当保洁的人
211院校大学生做保洁师的实用指南
作为90后,我后悔在深圳买了两套房
开了二十年出租车,他在老家买了两套房
辞职做保洁,治好了我的焦虑和失眠
一套房1000元,鹤壁在哪儿?
62岁退休教师做保洁,“找不到其他活,年龄超了”
51岁的退休阿姨,在四线城市逐梦互联网
“爸妈常年996工作,我最依赖的是他们请的阿姨”
家政中介“签单”秘术:涨不停的合同,流水的阿姨
网址: 我的保洁阿姨,在北京买了套房 http://www.xishuta.com/newsview113081.html
推荐科技快讯

- 1问界商标转让释放信号:赛力斯 95203
- 2人类唯一的出路:变成人工智能 21024
- 3报告:抖音海外版下载量突破1 20955
- 4移动办公如何高效?谷歌研究了 20186
- 5人类唯一的出路: 变成人工智 20185
- 62023年起,银行存取款迎来 10317
- 7网传比亚迪一员工泄露华为机密 8472
- 8五一来了,大数据杀熟又想来, 8452
- 9滴滴出行被投诉价格操纵,网约 8075
- 10顶风作案?金山WPS被指套娃 721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