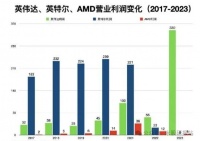在华北农村,成为“一日新娘”
在华北平原的一些农村,光棍是入不了祖坟的。按照当地说法,光棍入祖坟,会使得家族里代代出光棍。这一习俗延续了数百年,甚至更久。为了入祖坟,有人选择了死后配阴婚。而近几年,他们又想到了新的破解之道——找个女人结一天婚,不领证,不入洞房,只办一场结婚仪式就算成家。一些女性因此成为了“一日新娘”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冷杉故事 (ID:fhzkfirstory),作者:李禾,编辑:雪梨王,题图来源:视觉中国
接亲的黑色本田轿车在一家“休闲按摩”店前缓缓停下。婚车后面没有车队,车头上没有鲜花,车身上也没贴个“喜”字,甚至连新郎宋大志都没在车里。
宋大志61岁,是村里仅存的老光棍之一——在冀中平原东部这个1000多口人的村子里,算上宋大志,总共有5个老光棍。“在我们这里,一般过了35岁还不成家就被叫光棍,五六十岁没结婚,就叫老光棍。”有村民操着当地方言一本正经地解释,他说宋大志人品挺好,就是“太老实、太穷”。
憨厚老实、木讷迟钝的性格,外加家境贫穷,使得宋大志在婚姻市场的资源竞争中处在下风。而随着年纪越来越大,这件事愈发困扰他——他担心自己死后入不了祖坟。在当地以及周边很多农村都认为,光棍入祖坟,会使得家族里代代出光棍。也因此,没人愿意自家祖坟里埋个光棍。

当地人认为,光棍入祖坟,会使得家族里代代光棍。电影《光棍儿》剧照
不久前,有人给宋大志联系了一桩婚事,建议他找个女人结一天婚,不领证,不入洞房,只办一场结婚仪式就算成家了,这样死后就能入祖坟。
在当地以及周边农村,这种“一日婚”的情况隐秘地存在了许多年——但没人说得出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本地媒婆吴姐记得,大约五六年前,有人给她打电话,说想要个“一日婚”新娘。那是她第一次听到这个词。而今,吴姐手上“一日婚”的价位是新娘3600元,另有1000元的中介费和给伴郎伴娘的几百元红包。
接亲
宋大志的婚礼选在了6月中旬,日子是村里风水先生看过的,新娘住在60多公里外的邻县。这场婚礼之前,宋大志从未见过新娘,只知道她不满50岁,没有残疾。性格和长相对宋大志来说不重要,“反正就办一天事,是个女的就行。”
接亲的车去接新娘。宋大志坐在家里等着,同村的几个光棍朋友结伴过来道喜。他们和宋大志年纪相仿,有人光着膀子,讲究点儿的,穿了件布满污垢的短袖T恤,在门口的礼金桌上掏了份子钱——分别为20元、30元和50元。
“恭喜,恭喜啊。”一个老伙计说。宋大志憨笑,“可累死了,娶媳妇真累。”这话把另一个伙计惹笑了,“就娶一天,又不过日子,累啥累!”
站在一旁的人半开玩笑地建议,“你再多掏点钱,让新娘睡一夜呗。”宋大志不高兴了,“你真是个牲口,这么多小辈儿在这呢,胡说啥。”
随后,他们安静地坐在院子里嗑起了瓜子。

一名结过“一日婚”的男子的家。摄影:李禾
本田轿车开到按摩店门口的时候,新娘田丽丽正在店里梳妆打扮。这个48岁的女人没有礼服,也没有鲜花和红盖头。作为从事一日婚的职业新娘,她说不清这是自己结的第几次婚了,但她知道,只需要办完这个仪式,完成任务,就能赚到三四千块钱。而她在按摩店当老板,每月也只能赚几千块钱。
来接亲的宋金才是宋大志的堂弟,57岁,也属于“老光棍”的范畴。眼看堂哥结婚,他心里不太得劲儿,接亲这天,他甚至都没换件干净衣服——上身是穿了几天的黄色“史丹利”复合肥T恤,领口处泛着一圈黑乎乎的垢渍,两个裤腿上沾满密集的泥点,像是刚从田里劳作回来。
站在拉着卷闸门的按摩店前,宋金才摸出手机,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半分钟后,卷闸门“哗”的一声打开,宋金才小声嘀咕,“还真是个小姐!”
这话被店里一个60多岁的女人听到了。她就是刚才接电话的人——媒婆吴姐。“老宋啊,可不能胡说呀。这是正规按摩,男女都给按。现在是法治社会,谁干那些呀。”她有些不高兴地怼着宋金才。宋金才不想反驳,眼看快八点了,他只想接了人赶快出发。
吴姐把宋金才引进店里,让他坐下等会儿。这家56平米的按摩店,进门处放着两个红色沙发,再往里走是一张按摩床,床边矮桌上放着几瓶按摩精油和一摞面膜。老板田丽丽平时就住在按摩店里,“卧室”与“客厅”被一条淡黄色的劣质窗帘分隔开。
在沙发上坐了几分钟,宋金才有些不自在了,他受不了店里浓郁的香水味。田丽丽看他起急,加快了梳妆速度,很快从“卧室”走了出来——她中等身材,微胖,单眼皮、塌鼻梁,由于粉底打得很厚,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婚礼这天,她给自己挑了件咖色风衣、黑色紧身裤和红色皮鞋,把一条手绢绑在右手腕,天热时可以用来擦汗。
“挺好,挺美,赶紧走!”在吴姐的催促下,田丽丽上了车。
“紧张吗?”坐在后排,她被问到一个新娘们常见的问题。
“不紧张,你要每个月结几次婚,也不会紧张。”田丽丽面无表情,正襟危坐。
一路上,车子又接了伴郎和伴娘——一个50多岁、一米七左右,脖子和手腕上戴着油光锃亮手串的男人,和一个身穿绿色连衣裙,手腕上同样缠着手绢的女人。
这个由媒婆、职业新娘、职业伴郎伴娘组成的女方亲友团,赶往宋大志家。
光棍儿
大约一个多小时后,车子停在了宋大志家门口。虽说只是“一日婚”,宋家人也为此做了些准备。他们在外墙贴上了“良辰美景 张灯结彩”八个大字,院子角落贴着大大的“喜”字。
但这些还是掩盖不了院子的破败——三间房子是30多年前盖起来的,墙上的红砖早就褪了色,有的窗框上连玻璃都没有。院子没有硬化,裸露的黄土地上种着几株南瓜和两排辣椒。在村里,宋大志家人丁兴旺,他有一个哥哥、两个弟弟、一个妹妹,和一堆表兄弟和堂兄妹。大家日子过得还算安稳。
“讨老婆”是宋大志未竟的“事业”——早些年,女方嫌他穷。在门当户对和男高女低的传统婚嫁模式下,像他这样固守着三间老房子的底层男性,连辆自行车都没有,更遑论结婚生子。40多岁时,有人给他介绍过一个双腿残疾的女人,大他10岁。女方到宋大志家看了一圈,这门亲事就黄了。自那之后,再也没人给他张罗过亲事。
在华北农村,“光棍”被认为是最大的失败者。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陶自祥在博士论文中提到,对这里的成年男子来说,脱离父母的旧家庭,而自身倘若没有组建新家庭的能力,生活没有家庭作为载体来参与社区性互动,其生命意义会被认为是无法实现的,“在华北平原,‘光棍’是没有资格来过日子的,一个光棍的‘家’在华北平原没有任何社区性文化意义。这样的家庭受到村庄强烈的身份排斥”。

死后进不了祖坟,对光棍们来说是很大困扰。摄影:李禾
起初,宋大志和父母住在一起,生活起居还算有个照应。2011年、2013年父母相继去世后,他的生活变得一团糟。他不爱干净,喜欢在外面捡垃圾,把垃圾堆放到屋里。天气一热,屋里总有股馊味,很多人因此把他当成“流浪汉”或“傻子”。
平时除了务农,或是到镇上建筑工地打工外,他总爱跟村里的其他光棍凑在一起。几个人聊得最多的,除了挣钱,就是女人——谁长得好看,谁成了寡妇。宋大志想过找个寡妇搭伙过日子,他打听了一下,听说对方要彩礼,得备上金镯子,就没敢再惦记。也有人给他建议花三五万,去买个云南或者越南的老婆,宋大志还是嫌贵。实际上,他有十几万存款,可得“留着防老”。
一个人熬了一年又一年后,宋大志恐慌起来。光棍入不了祖坟,对他来说,意味着无法和父母地下团圆。这个习俗在华北平原延续了数百年,甚至更久。至于光棍如何安葬,各地做法也不相同。以河北省为例,有的会随便给找个地方埋了,有的则会葬到离祖坟不远的位置。
2022年下半年,宋大志跟哥哥说起自己的担忧。哥哥安慰他,大不了配阴婚——这一至今流行于河北、河南、山东、山西等地的封建陋习,是指为自己家里死去的人找寻“配偶”,把他们作为夫妻的名分葬在一起。“但阴婚对象很难找”,有当地的易经研究者透露。
2023年4月中旬,村里其他光棍告诉宋大志,县里有人结了“一日婚”,并说这种形式等同于结婚,死了能入祖坟。宋大志立马托人打听。最终,在县城工作的弟弟辗转打听到了媒婆吴姐的电话。吴姐很热情,说新娘随时有,收费3600元,中介费1000元,伴郎伴娘给几百元红包就可以。她催宋大志赶紧把日子定了,说想要结“一日婚”的人太多,排不过来。
至于新娘,按照规矩,婚礼前是不能见的。“你就瞧好吧,我这边的新娘质量,在全市都是最好的。”吴姐不肯透露新娘的年龄、籍贯和婚姻状况,担心她们个人信息暴露太多。
“就和开盲盒一样。”宋大志的弟弟觉得。
婚礼开始了,新娘和新郎被安排坐在屋前空地的椅子上,接受亲戚们的祝福。宋大志显然有些紧张,一直不敢靠近新娘,田丽丽则始终保持微笑。围观的人开始起哄,有人让他俩拥抱一下,有人怂恿宋大志亲吻新娘。宋大志躲闪着,直到家里一位长者宣布婚礼开始,“今天是美好的一天,宋家老二要结婚了……让我们祝福这对新人和和美美,白头到老。”
夫妻对拜环节,宋大志敷衍地低了低头,田丽丽深鞠一躬,看上去很真诚。
婚礼的最后,两人被车子拉到1公里外的父母坟前跪拜,点香、烧纸、磕头。宣布婚礼开始的那位长者对着墓碑郑重地说,“你们家老二结婚了。好好看看,这是新娘子。以后一家人就能团聚了,放心吧。”
仪式完成后,女方亲友团没再去婚宴现场。整场婚礼,宋家支付给媒婆5600元,其中田丽丽分到3600元,吴姐拿走1000元,伴郎伴娘各分500元。
“一辈子有这么一回,值了。”宋大志觉得挺好,礼金收了几千,自己的存款几乎没动,“这不比配阴婚划算多了。”他把两人合影贴在衣柜镜子上,照片一角印着“百年好合“四个字,“等我死后,把这照片放进棺材,这是我的结婚证明。”
吴姐很忙
宋大志的婚礼还没结束,吴姐的下一单生意就来了。
“他们都觉得我是活菩萨。”接完客户电话,她的眼睛笑得眯成一条缝。吴姐比宋大志大6岁,可比他显得年轻。她喜欢穿碎花衣服,把花白头发染得乌黑。相比起跳广场舞和拉家常,她更享受当媒婆。
平日里,只要有陌生电话打进来,她会立马接听——男的喊“老弟”,女的年长的叫“老姐姐”,稍微年轻的叫“老妹”,再小一点就是“大妹子”。如果是介绍对象,她一般会大声连说三次“没问题”,让对方加自己微信,再跑去给对方的朋友圈挨个点赞。
吴姐说自己用年轻人的话讲,叫“社牛”。大约十几年前,有人找她撮合了一起婚姻后,塞了200元钱红包给她。她忽然意识到,或许可以把媒婆当成副业,这比平时务农主业要轻松许多。那之后,她开始留意十里八乡的单身男女,也时刻关心谁离婚或是丧偶。
“现在的年轻女孩、小伙子很多在外地上学,回家后认识的人不多,要想找对象,很多得靠媒婆。”吴姐的生意还不错,“我们老家,半个村的婚姻,都是我介绍的。”
她早年的业务范围里,没有“一日婚”。“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。”吴姐记得,大约五六年前,有当地人给她打电话,说想要个“一日婚”新娘。吴姐听了觉得挺荒谬,“那不是连人带鬼一起糊弄吗?”可电话那头态度很真切。吴姐仔细一想,或许这是门新生意。
于是,她四下打听相关信息,并拿到了邻县一个媒婆的电话。
一顿饭的功夫,吴姐学到了门道。这其中,“最难的就是找新娘子”。回到本县后,她开始寻找在当地工作的外地保姆、按摩技师。坚决不找本地人,是担心“影响不好”。
她招到的第一个新娘,是一个50多岁的外地保姆。丈夫去世后,从家乡到这里随外嫁的女儿生活。男方则是邻县农村的一个光棍。这笔生意下来,新娘拿到2000元,吴姐拿到600元。此后,靠着口口相传,吴姐的生意慢慢好了起来,陆续招到了6个外地新娘。
新娘并不好找,“最主要都觉得丢人,没人愿意干”。对于选新娘的标准,除外地人外,吴姐还开出两个条件——不超过60岁、身体没残疾。起初,她想找退休人员或在饭店打工的女性,但不光找不到,还总被骂“老不正经”。
经历了几次失败后,她把选人目标锁定在按摩店,以及保姆群体。
吴姐手上的新娘不论年龄长相,一律统一定价,“那些光棍汉根本不挑年龄。我也想找更年轻的,30多岁最好,可没人干。”时间久了,吴姐的雪球越滚越大,其他县的人有时也会慕名找来。而这种生意恰恰是正规婚介机构很少去做的,在他们看来,“那不就是骗人嘛,我们不想出事。”

两张图中的新娘为同一人,她至少与两名光棍结过婚。受访者供图
吴姐所在的县城周边,还隐匿着不少类似的媒婆。她们的操作流程大抵相同——不提前透露新娘信息,也极少在婚前安排新郎和新娘见面。如果强行要求见面,有媒婆会提出让男方带身份证,并且“不能说话,只能远远看一下”。此外,每个地方收费也不大一样,便宜的一次三四千,贵一些的五六千。有媒婆直接开价两万元,“过夜的话,再加2000元。”对于过夜一事,大多媒婆是拒绝的,“那不是介绍卖淫嫖娼吗?”
“不管是新郎还是新娘,他们都是可怜人,我们是在帮他们。”在吴姐看来,这种做法没有任何不妥。仅仅靠着做职业新娘的生意,吴姐每年能赚四五万,“比县里拿退休金的老太太挣得多。”她的丈夫和儿子也支持她。为方便母亲联系业务,大儿子还把她接到县城居住。
“咱是帮人结婚的,不是拉皮条的。”吴姐说,“不信你问小田,我啥时候要求她们过夜?”
县城里的外地女人
小田,就是田丽丽。她是吴姐手头目前最年轻的新娘。
和宋大志办完仪式被送回按摩店后,她马上去附近农行取款机上把钱存到自己的卡里,准备等老家的丈夫没钱时给他转过去,“店里人来人往的,放很多现金不安全。”话是这样说,但实际上,她的按摩店生意并不好,附近小区的居民更愿意去不远处的盲人按摩店。
这让田丽丽有些不爽。她觉得总有人给“休闲按摩”贴色情标签,她坚称自己从事的是正规按摩。为了证明自己的专业,田丽丽展示了她取得的,一本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监制的《职业资格证书》,证书里面类别为“保健按摩师”。
田丽丽在足疗按摩行业做了20多年,辗转过沈阳、昆明、武汉、合肥等地。就连她的丈夫,也是在足疗店打工时认识的同店保安。结婚后的前两年,他们还在同一个城市工作。孩子四五岁时,丈夫带着孩子回了老家,平时在家务农,偶尔打打零工,家里大部分开销都是田丽丽承担。就这样,她一直把孩子养到了21岁,大专毕业。
只有过年时,她会回老家待一周。孩子对她似乎没什么感情,“明显和他爸更亲”。
对孩子和丈夫,田丽丽谎称自己是在做保姆——她也的确做过一段时间保姆。在老乡的介绍下,她到北京照顾失能老人。可这份工作太熬人了,她几乎全天都要待在老人家里,给她喂饭、翻身、按摩、端屎端尿,没有任何喘息时间。半年后,她离开了老人家。
有老乡建议她报个按摩培训班,她报了,学得很认真,也顺利拿到了证书。起初,她在北京一家按摩店上班,不到一年店铺倒闭,她又失业了。田丽丽本想留在北京继续找工作,可年过40,随着身材走样、皱纹不断增多,她在这座城市的求职市场上没有丝毫优势。在去一家盲人按摩店应聘时,老板甚至因为她不是盲人,没有要她。
在北京兜兜转转,田丽丽的压力越来越大。就在她想回老家发展的时候,之前工作过的按摩店老板打来电话,说在距北京几十公里外县城开了一家按摩店,希望她来帮忙。
县城位于北京、天津、保定的三角地带中心,是个传统农业县。和北方很多县城一样,这里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工作。留在当地的,过着乏味的生活——打工、逛夜市,偶尔去下KTV。
那年,田丽丽43岁。县城里的这家按摩店里算上她,一共只有两个员工。为了防止田丽丽和同事接私活,老板在店里装了监控,客人日常消费扫的二维码是连接老板的。
彼时算上提成,田丽丽每月能挣五六千元。疫情之后,生意陡然下降,老板想要关店。对田丽丽来说,这意味着她无处可去了。于是,她提出接手店面,自己当老板。
“就当租房住了。”田丽丽说,店里租金每月5000元,为了节约成本,她辞掉了之前的同事。疫情反复下,店里生意时好时坏。坚持到2021年下半年时,她的人生再次发生变化——一个常来按摩的老太太突然说要给她介绍个兼职。这个老太太就是吴姐。
听说要和光棍结婚,田丽丽一阵恶心,没答应。但每次吴姐来按摩,总要跟她念叨这事,还给她看其他职业新娘的视频——视频中,新郎新娘端坐在院子里接受大家围观,似乎没什么出格的事。吴姐用来说服田丽丽的理由是,“就大半天时间,反正是你外地的,谁也不认识”。她还保证,绝不过夜,不会领证,更构不上重婚罪。
当店里生意越来越差时,田丽丽心动了。她向吴姐提出“不透露身世、不安排过夜、不发送照片”的要求,否则“谁都别好过”。
“新娘”
2021年冬天,时年46岁的田丽丽接了首单生意——一个当地农村光棍,为了死后能入祖坟,找吴姐安排一日婚。当时,新娘的费用只有2000元。
第一次做职业新娘,田丽丽有些紧张,她担心会暴露。为此,她化了浓妆,戴了一顶齐腰的黑色假发,衣服也由钟爱的黑白灰色,换成了粉色旗袍。外形与平时的自己判若两人。
男方是个70多岁的老头。尽管田丽丽做了很多心理建设,但眼看要和自己父亲年龄相仿的人拜堂,她只能强忍着反胃。“当时大脑一片空白,只记得些片段”,田丽丽说,这些片段,包括有人强行将两人脑袋紧贴在一位,有人趁乱摸她的后背与臀部。最让她别扭的,是和新郎到坟地下跪,对着不认识的人喊爹妈。最终,她拿到了2000元现金,几斤糖果、瓜子,以及香烟和白酒。

一名正在结“一日婚”的男子。摄影:李禾
回到按摩店后,她还是觉得反胃,但又不想就此退出,“大概还是为了多挣些钱吧。”用了两三天后,她和那些情绪和解了。她给吴姐发微信说,“这次谢谢了,以后多合作。”
没过几天,吴姐给她介绍了第二单生意,男方老家也是当地农村的。这一次,田丽丽没那么别扭了。随着结婚次数越来越多,她逐渐专业起来,不仅克服了反胃,还能保持微笑。但她尽量不开口说话,以免熟人通过声音认出自己。每次,她都要化浓妆、戴假发,只是穿衣没那么在意了,觉得“穿什么无所谓”。
两年多下来,田丽丽和当地一些光棍结了婚,也与邻县一些光棍结过。结婚费用由最初的2000元,变成了2500元、3000元,直到现在的3600元,“有时候一个月结十几次,有时候两三次。除了疫情严重的时候,几乎每个月都有婚礼。”这让她变得习惯和麻木。有几次,她还和同村的多个光棍结婚,“就是和一个老头结婚后,没多久又和同村老头结婚了。”有时在婚礼现场,还会有之前的“丈夫”来围观。
田丽丽说,自己最后的底线是“不过夜”。也的确有光棍提出过加钱过夜的要求,她一概拒绝了,“我只是当新娘,不是当小姐。”为了避免闲话,她几乎不主动交当地朋友,有客人按摩时问起她的家乡,她也会随口说个省份。
靠着这个“副业”,她养活着自己、按摩店,远方的丈夫和孩子。
丈夫一直以为田丽丽在北京做保姆。今年5月,她险些露馅。彼时,她和一个光棍结婚的视频被人发到短视频平台,刚好被丈夫刷到。他把视频转给她,“这个人很像你”。
田丽丽吓出一身冷汗。她赶紧解释,“是挺像,但不是我,我在北京呢。”为了制造在北京工作的假象,她时不时乘大巴去北京,在一个固定的小区门前给家里打视频电话,证明自己在北京。到北京后,她还会拍些有明显标志的视频和图片,保存起来,回到县里后再隔三差五用这些发朋友圈。
前段时间,她和宋大志结婚时,就在朋友圈发了张自己在陶然亭公园的留影,配文写道,“今天真热,来公园避暑是不错的选择”——这条信息,有12个人点赞,其中有田丽丽的丈夫,也有媒婆吴姐。
日渐麻木没能让田丽丽变得更快乐,她还是觉得做职业新娘不道德。为了让自己得到救赎,她信过教、拜过佛。她告诉“上帝”和“释迦牟尼”,自己是在帮别人入祖坟,从没有害人之心。她也想过离开这个行当,“真没人逼我干这个,可我还能做什么呢?”每次郁闷了,她就找吴姐吐槽。后者开导她,“什么都是假的,只有钱是真的。”
6月中旬搞掂了宋大志的婚事后,吴姐又接了两次活儿,新娘都是田丽丽。7月2日上午,她突然接到宋金才的电话。帮堂哥接亲后,他在家犹豫了一阵,提出想结“一日婚”。
“老弟,你就瞧好吧,上次和你哥结(婚)那个行不行?”吴姐又一次推荐了田丽丽。
“还是换个吧。”宋金才吞吞吐吐起来,“咋说也是我嫂子,总觉得不太好。”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所涉采访对象均为化名)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冷杉故事 (ID:fhzkfirstory),作者:李禾,编辑:雪梨王
相关推荐
华北的“蔚小理”还要等多久?
每天有一万件婚纱从安徽丁集镇发出,去为中国新娘造梦
农村娶媳妇要花100万?农村男女城市化差距的窘境
巨头们AI的角力战正向农村渗透
金融科技在印尼(下):到农村去,到下沉市场去
我在印尼农村做下沉电商
在智能摄像头里,看见一个微缩农村
彩礼和嫁妆背后的经济逻辑
农村电商难在哪里?物流低效,用户难以留存
翟欣欣案性质盖棺:暗黑蛇蝎版“落跑新娘”的倒掉
网址: 在华北农村,成为“一日新娘” http://www.xishuta.com/newsview82415.html
推荐科技快讯

- 1问界商标转让释放信号:赛力斯 95273
- 2人类唯一的出路:变成人工智能 21579
- 3报告:抖音海外版下载量突破1 21553
- 4移动办公如何高效?谷歌研究了 20718
- 5人类唯一的出路: 变成人工智 20712
- 62023年起,银行存取款迎来 10377
- 7五一来了,大数据杀熟又想来, 8945
- 8网传比亚迪一员工泄露华为机密 8569
- 9滴滴出行被投诉价格操纵,网约 8567
- 10顶风作案?金山WPS被指套娃 7258